《二十四城记》剧情介绍
曾经的繁华荣耀,随着时光流转与时代变迁渐渐褪去耀眼的光环,留下的则是无尽的落寞与慨叹。420厂(成华集团),一座从东北迁至四川的飞机军工厂,在特殊的年代里它曾是无数人羡慕与自豪的所在,然而和平的气息和体制改革却将它的光鲜逐渐销蚀。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它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转型的阵痛,而今旧厂址易作他主,一片现代化的楼宇将拔地而起。 大丽(吕丽萍 饰)、小花(陈冲 饰)、娜娜(赵涛)以及众多新老员工见证了厂区几十年的变迁。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万千唏嘘连同那旧日回忆随风飘散……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一屋两家三姓人蓝色罗曼史无限纯白的你泪洒女人花灵幻大师光盲青春甜孙爷爷里基·莱普与夜鹰天启Z:完结的起点绘画正义小包公兄弟如手足天空战队恰似你的阳光红尾鸽叠积瓦舍之素舞遥公主夜游记猛男香水店巴黎大饭店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身体互换情诗婚礼进行时商魂猛男军中鬼故事惊爆银色选战前田建设梦幻营业部甜心巧克力满城尽带黄金甲
《二十四城记》长篇影评
1 ) 三个关键词
工厂:《二十四城记》的故事发生地是成都420厂,老工厂的空间感,重型机械重量感,斑驳的历史感非常有特色点;420厂让我想起《三峡好人》中的那个被拆迁的化工厂还有王兵《铁西区》中的炼钢厂。
这些曾经的国有企业有着辉煌的历史和无上荣光,有着感人肺腑的故事和记忆,《二十四城记》非常好的找到一个切入点,把历史和现实、光荣和凄凉的剖面呈现给观众,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
从农民到工人,从县城到工厂,贾樟柯的电影触角逐渐深入中国这个面庞上的皱纹深处,掬取隐藏着的尘埃和眼泪,让我们再次注视那些在身边走过的卑微的面孔,让我们再次被打动。
纪录:《二十四城记》是部纪录片,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尽管其中设置了几段演员表演的故事,但是这几段采用纪录片手法拍摄的,这几段故事有生活的原型,演员模拟原型搬演生活,尽管不是原型本人,但我以为这和原型自述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影片还是部不折不扣的纪录片。
其实对于《二十四城记》探询影片类型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是他呈现了什么给大众。
广告:《二十四城记》在开拍之际就饱遭“为地产商拍广告”的非议,批评者众;这种批评一度影响了我对影片的期待,但是我相信只要是贾樟柯的电影再次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即使他是在拍一个广告电影。
事实上《二十四城记》确实不差,而且好的超过我的想象,所以我为贾樟柯欣喜。
不可否认《二十四城记》是个广告痕迹非常重的电影,但他竟然可以让你忽略片中如此重要的广告,按照工业术语这叫广告与艺术超完美的无缝焊接.
2 ) 《二十四城记》/诗摘
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二十四城记》引用诗集古诗,“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花”,据说是因为宋人赵忭在《成都古今记》中记载说:“五代时,孟蜀后主成都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锦城。
”因此才有二十四城的诗句,再现了彼时“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的成都。
另外:“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花”这句诗仅在罗念生《芙蓉城》里提到过,原始出处不详。
上下两句的尾字都是“花”,第二个花应该是“华”的通假字。
沈韶(明)《琵琶佳遇》中有“吴中自昔称繁华,回环十里皆荷花”。
宋英宗时,赵汴曾为成都长官,作《成都古今记》记载道:“五代时,孟蜀后主于成都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二十四城”的来历在该书中或许应有记载。
《玻璃工厂》 欧阳江河一从看见到看见,中间只有玻璃。
从脸到脸隔开是看不见的。
在玻璃中,物质并不透明。
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它的白天在事物的核心闪耀。
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就象鸟在一片纯光中坚持了阴影。
以黑暗方式收回光芒,然后奉献。
在到处都是玻璃的地方,玻璃已经不是它自己,而是一种精神。
就像到处都是空气,空气近于不存在。
二工厂附近是大海。
对水的认识就是对玻璃的认识。
凝固,寒冷,易碎,这些都是透明的代价。
透明是一种神秘的、能看见波浪的语言,我在说出它的时候已经脱离了它,脱离了杯子、茶几、穿衣镜,所有这些具体的、成批生产的物质。
但我又置身于物质的包围之中,生命被欲望充满。
语言溢出,枯竭,在透明之前。
语言就是飞翔,就是以空旷对空旷,以闪电对闪电。
如此多的天空在飞鸟的躯体之外,而一只孤鸟的影子可以是光在海上的轻轻的擦痕。
有什么东西从玻璃上划过,比影子更轻,比切口更深,比刀锋更难逾越。
裂缝是看不见的。
三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说出。
语言和时间浑浊,泥沙俱下。
一片盲目从中心散开。
同样的经验也发生在玻璃内部。
火焰的呼吸,火焰的心脏。
所谓玻璃就是水在火焰里改变态度,就是两种精神相遇,两次毁灭进入同一永生。
水经过火焰变成玻璃,变成零度以下的冷峻的燃烧,像一个真理或一种感情浅显,清晰,拒绝流动。
在果实里,在大海深处,水从不流动。
四那么这就是我看到的玻璃——依旧是石头,但已不再坚固。
依旧是火焰,但已不复温暖。
依旧是水,但既不柔软也不流逝。
它是一些伤口但从不流血,它是一种声音但从不经过寂静。
从失去到失去,这就是玻璃。
语言和时间透明,付出高代价。
五在同一工厂我看见三种玻璃:物态的,装饰的,象征的。
人们告诉我玻璃的父亲是一些混乱的石头。
在石头的空虚里,死亡并非终结,而是一种可改变的原始的事实。
石头粉碎,玻璃诞生。
这是真实的。
但还有另一种真实把我引入另一种境界:从高处到高处。
在那种真实里玻璃仅仅是水,是已经或正在变硬的、有骨头的、泼不掉的水,而火焰是彻骨的寒冷,并且最美丽的也最容易破碎。
世间一切崇高的事物,以及事物的眼泪。
《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 贾樟柯/侯丽君(受访工人)人有事做,老得慢一点。
《随时间而来的智慧》 叶芝(爱尔兰)Though leaves are many, the root is one;Through all the lying days of my youthI swayed my leaves and flowers in the sun;Now I may wither into the truth.秋叶繁多,根只有一条;在我青春说谎的日子里,我在阳光下招摇;现在,我萎缩成真理。
《红楼梦·葬花吟》 曹雪芹(清)怪侬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泼了的牛奶》 叶芝(爱尔兰)We that have done and thought,That have thought and done,Must ramble, and thin outLike milk spilt on a stone.我们曾经做过的和想过的,曾经想过的和做过的,必然漫开,渐渐地淡了象泼在石头上的牛奶。
《本质》 万夏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人终究不尽完善太多的机会都留在错误中我们却在幸福里得到进步说和做并非本质喝酒的时候口含一颗樱桃我们可能错读一本书认识一群内心脆弱的人物为那些被粉碎的东西伤心和痛哭这些也不是本质最高最完美的是一些残缺的部分我们完善的两次事件之间这一切又仅仅是过程你祈求和得到的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3 ) 《二十四城记》:没有快感也能喊,真是奇了怪了
题记:人在很投入的做爱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呻吟。
人难免有时候会有些应酬,即使没快感也要装作投入,例如卖淫的时候,给领导过生日的时候,党会上鼓掌的时候……——魏晓波在这部电影里还是能找到以往贾樟柯电影中的元素,每遇到一次,就会被舒服一次。
例如巧妙的配乐,例如缓缓的摇镜头,例如梦境般的过去和惨淡的现在。
但是除了这些,《二十四城记》呈现出的是一种让我觉得反感的假。
早期的片子还是以“纪实”风格取胜的。
我始终觉得《小山回家》和《小武》呈现出的粗糙是惊艳的的,独一无二的。
后来的片子虽然看起来还是很纪实,但是故事性和戏剧性都大大的增加。
剧情片毕竟不同于纪录片,它没有还原真实的责任,它要做的是以作者的主观视角呈现作者脑子中的“真实”。
《二十四城记》当时如果拍成一个纪录片,会是一个不错的片子。
但是,贾樟柯有了投资商。
我觉得有投资商是个好事,但是拿了投资商的钱应该拍部像样的片子出来,对得起那些钱。
影片中的几个真实演员的部分先不说。
吕丽萍、陈建斌、陈冲、赵涛等人那都是演了些什么玩意。
吕丽萍讲的故事够惨,但是不是亲娘谁都演不出那种丢了儿子的痛。
陈建斌为了使表演更加真实,还假装咳嗽。
陈冲演的像上海人,但是压根看不出一点工人的痕迹,脸可真够光滑的。
赵涛演的还像,但是怎么看都让人想起他在贾的其他电影中的样子。
这些演员都是著名演员,观众都认识。
这是一个讨厌的提前。
所有电影导演在用大家都认识的演员的时候首先要做到的是设法使观众忘记这个人是凯特•温丝莱特,这个人是“汉娜”。
这里我说到的“设法”包括化妆(这是最幼稚的办法),还有设置剧中人物的生活场景,说话方式等等。
吕丽萍拿着一个盐水瓶走,这个不足以使观众认可这是一个工人。
所以,这一群演员用的很蹩脚。
还有,导演在刻意的往影片里塞“历史大事”,非要把人物的小命运和时代的大背景联系起来。
例如抗美援朝、周恩来去世等。
填一两条就足够了,怎么每个人都有历史大背景?
这就有些刻意了。
虽然,中国这个荒谬的国家,每个人的历史都被政治不断的改变,每个人的历史都是国家的历史,因为国家总是掺和和操纵个人。
但是,把这些都说出来,除了给人意淫一下,其他作用就很轻了,历史并不重要,个人的命运比历史更重要,历史甚至都不需要出现我希望我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贾樟柯是对的。
我希望有一天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嘲笑好多填前或者好多年前的魏晓波。
还有,贾樟柯叫的那声“小妹妹”很撩人。
魏晓波2009-3-21于长沙
4 ) 24城记 贾樟柯将走向何方
“他已经忘记了,电影是由流动的画面构成的。
”2007年去世的欧洲艺术电影大师伯格曼曾经这样批评安东尼奥利的某些电影。
就在24城之前,贾樟柯的制片潘剑林导演制作了一部让许多人目瞪口呆的电影——《夜未央》,并不是因为他对外宣传的题材问题,而是他将整个电影变成了一部访谈录,配以少量的隐喻画面,将语言在电影中的功能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
这样的电影风潮大概是从阿巴斯2002年的实验电影《十》开始的,沿着某种被命名为大师的小路缠缠绵绵的传到了中国。
可是如果我们只需要字幕的话,电影又在什么地方存在呢?
当你看过从《十》到《夜未央》之后,也许你对《24城》就更有承受能力了,至少贾樟柯顽强的保留了他的贾氏美学,当你看到那些错过班车的人们,看到那两个始终在长城火箭下打羽毛球的男人,看到那些与工厂融合在一起的脸庞,你也许还会想到,贾樟柯依然是那个时常带来惊喜的导演,那个让人们在标语口号下谈恋爱的男人。
但是当你有看到一个一个人旁若无人的叙述一些半真半假的事情的,特别是那个坐在空荡荡客车上的东北女人时,你是否会想起另一个人?
对的,就是阿巴斯。
当你看到演员从非职业过度到职业的时候,你是否又想起了一部戏?
对,就是那个《希林公主》,当阿巴斯以与职业演员合作是致敬作为理由的时候,你真的相信么?
就如同我看到吕丽萍时的感觉一样,你以为我会真的相信贾樟柯是要达到什么什么效果么?
就是一个表演的效果。
他只是觉得自己某种推动的情绪在真实面前在逐步消失,于是他选择了表演,以及无休止的调色和诗句。
我承认那些颜色和诗句以及音乐都是玩弄得炉火纯青,总是恰到好处的击中了许多人的胸膛,可是这个真的是拍出《站台》的贾樟柯么?
是什么东西让他将现实的力量放弃了,是什么东西让他沉浸于语言的陈述,是什么东西让电影走得如此的艰难。
我不得不称赞他,多年以来他对电影的理解让他将所有的镜头都运用得如此成熟,也许更应该感谢的是,多年来的广告公司生涯,让他对那些当个镜头表演的情绪做得如此到位,我曾看见一个网友评论说,他的一个法国朋友也被24城感动的一塌糊涂。
我在想如果去掉那些音乐呢?
如果去掉那些本身就蕴含着巨大情绪的诗句呢?
他是被做电影导演的贾樟柯感动,还是被做广告导演的贾樟柯感动?
如果他也曾看过那部让许多法国人背着面包矿泉水坐足八个小时观看的《铁西区》,他是否还会回头看这部主观色彩极其浓烈的《24城》?
当贾樟柯当了多年老总回头,历史已经不再是历史,现实已经不再是现实,而是构成他心中史诗的一个素材而已,那个反复出现的工厂门口的巨大的俯拍,已然让人高高在上的去怜悯这段历史,怜悯那些穿着蓝色工作服如同蚂蚁一般的人们。
恕我愚钝,竟然不曾在三峡好人那两段超现实里看出贾樟柯的转变,可是难道贾导已然忘记,历史是流动的,时间是流动的,电影也是流动的。
当冯小刚不厌其烦的让他的演员在电影上说相声的时候,贾樟柯又加入了评书的行业。
5 ) 最感人的还是身边的生活啊~~~
看了池莉的《来来往往》后就接受了一个观点:我们不能否认一个时代,因为他是很多人的生活背景。
三线军工厂如此,以前多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这种类似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看到在自己身边发生过的故事,怎能不感慨!
6 ) 语录
人有事做,老得慢一点。
秋叶繁多,根只有一条。
在我青春说谎的日子里,我在阳光下招摇。
现在我萎缩成真理。
叶芝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万夏
7 ) 二十四城记:一个厂,一座城,一个国
厂是420厂,城不是成都,国却是当下的中国。
一、言说贾樟柯无疑是十足自恋的,这里的自恋没有任何贬义,而是说他对自己的电影方式和自己的生命情有独钟。
《二十四城记》在贾樟柯的作品序列中处在一处转折点,贾樟柯用这部影片对此前的作品做了一次有趣的总结。
原谅我只能用“有趣”这个词,当然也可以说是奇妙的,因为这部片子在我的视野里,是中国电影序列里仅见的“仿纪录片”(Mock Documentary指用纪录片手法和表象拍摄的故事片。
当然“纪录片”这个词本身也是裂隙纵横,至少包含了三种以上的不同影片类型,此处从略)。
而这次影片又像一次长长的注目礼,对贾樟柯自己的电影作品,更是对中国当代史的后半段——于是我知道贾樟柯无论是从表达欲到叙事野心,都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部影片显然是过分表达的,因为“表达”或者“言说”甚至成了直接的表象和影片的主部。
此前我与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在大银幕上看纪录片(无论是哪种的纪录片)的经验——最多是在教室看过投影。
这一次我的震惊体验大概与超级写实主义的油画类似,影院的大银幕上访谈和“访谈”的单调构图对我形成了极大的冲击。
而贾樟柯的策略,或者说影片结构,则是“真假参半”,用访谈和记录引入规定情境,然后再用一样的手法——被放大的“言说”——来进行叙事。
试想倘若不是吕丽萍陈冲赵涛陈建斌,那么她(他)们的“扮演”行为是不是仍然能够被指认?
或者,那些“受访者”同样也是在“扮演”?
这里涉及到摄影机本身的权力问题,也就是说在摄影机下展示出来的是否还是“真实”,那么贾樟柯的回应则是两种——第一,有且只有言说,而言说的内容只好请观众“脑补”(脑内补完);第二,用职业演员的扮演在某种程度上提示这一“言说”的实质。
换言之,我们并无必要去追究那些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当然可能有一个丢了孩子的母亲,在一本或者可能存在的《成发集团发展史》中有记载;或者也可能有一个酷似陈冲的上海姑娘——但是这些不是重要问题,重要问题在于这一切的呈现方式。
因为“言说”这一表象的存在,以及前30分钟的访谈和后75分钟的“访谈”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互文关系,有必要强调的是,“访谈”中的“故事”可能是特定场景下的故事,也可能是对生活的某种提炼。
实际上除了第一个访谈,此后的访谈都具备充分而完整的故事性,它们就是故事本身,由此也再次对故事进行了自指——贾樟柯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因为如果不用这种手法,这部片子要么是一个N段式电影,要么是一个依那里图式的多线交织的后现代故事片。
于是从这个表象入手,对《二十四城记》的解读就会完全改变,因为首先重要的不是影片内容而是影片的形式——对纯形式的解读完全可以导向某种意识形态批判。
当然可以把这种手法理解为缺少投资和缺乏能力——试想以这部高清数字电影的成本如何能cover一个跨越40年的史诗级别的故事?
但是我倾向于认为贾樟柯的这种手法是有意为之——至少他不隐藏导演和摄影机,并且曝露了故事的讲述机制。
二、叙事或许刚才的分析会导致对这部电影“形式大于内容”的判断。
而就影片试图表达的内容而言,无疑是大大溢出了影片的范围。
影片呈现的是一段历史,那么这部影片自然进入“当代史叙述”的序列中。
420厂的历史,与中国当代史基本是等价的——从“以小见大”的角度来说。
虽然当代史的禁区依然是禁区,比如文革(第一段访谈里的武斗),比如八九(好像与本片没有关系),但至少贾樟柯还讲到了不可绕开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去年对新时期的回顾之中绝少提到的话题。
当然大书特书的则是93年资本主义化进程开始之后的“分享艰难”,呈现方式则是讲述之中对“昔日荣光”的怀念和受访者无一例外的眼泪。
贾樟柯最娴熟的技巧——用流行歌曲来标定时代——又一次成了他在影片中的签名,也是他一贯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结构当代史的方式。
受访人物的出场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从建厂之初一直到现今的“80后”。
一共8个受访者,其中4个演员,3个“真人”,剩下一个赵刚——大概能各算一半吧。
这也是颇具形式感的安排。
贾樟柯并无意通过他们的讲述构筑一个整体的叙事,但这些生命片段的交织却产生了某种蒙太奇层面上的意义。
其实一个人的生命,讲述出来不过也是如此几句。
在这些讲述之中,我们得知了420厂的变迁——它着实是一处“飞地”,如《世界》里的世界公园一般,超大规模的移民,一个工厂甚至成了一个小型规模的城市——有学校、电影院、游泳池,大量穿着统一制服的工人——大型国有企业的普遍处境。
似乎用“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来下按语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部影片里的“工人阶级”多久没有在影片中出现了?
曾经的“工人阶级专政”似乎也不再作为一个常见的提法了。
而最后工厂变成楼盘,似乎也是某种当下资本取得胜利的隐喻。
于是成都终于把曾经的飞地吞入肚中,荣光无限的工人阶级也光环不再,终于还是在社会巨变面前成了各谋生路的市民。
就“当代史书写”而言还可做出一篇大文章,但无论如何,贾樟柯这次展示出来的却是从《站台》一以贯之的视野,而《三峡好人》之中的潜台词——郭斌曾就职的工厂,以及作为“福建女老板”的翟永明开发的地产——在这里被详细的呈现。
贾樟柯作为“70年代生人”的自觉使得他对80年代的叙述格外地精彩,附带地也造成了某种断裂和含糊,尤其表现在某种“更久远”的历史的状态下。
三、观看贾樟柯的风格,或者说是“作者要素”,在影片中依然熟悉,比如逆光的窗户——得自侯孝贤的一种构图方式,还有很多,比如举着吊瓶的吕丽萍等等。
当然非常明确的一个前文本是《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同样在处理“拆迁”这个命题,于是很多镜头都很相似,贾樟柯式或者余力为式的小横移,但由于高清本身的问题使得运动镜头不太流畅,还有最后一个俯瞰成都的镜头,明明就是《三峡好人》的情绪的延伸。
于是《二十四城记》同样具有了某种史料价值,我曾在对《三峡好人》的评论中说“《三峡好人》真正所讲的故事是后工业时代中国的一个城市如何将要被废弃,如何正在一点一点消失,从而构建的一个关于现代社会的寓言。
”而《二十四城记》要讲述的则是更深刻和更直接的层面上的问题——不是因为要建水电站,而是因为资本的介入;不是一个城市的消失,而是某个与红色历史相关的“飞地”的最终消失——这是否也是对红色历史的某种评判我不得而知。
然而还可引起注意的是访谈人物的选取,女人——四个女人,尤其后三个,承担了不同程度上的悲剧。
如果不是毛的军工企业“靠山方针”,那么侯丽君的母亲与外婆是否不会分离十几年,是不是那么多东北人不用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四川,是不是大丽丢失的孩子能够被找到,是不是顾敏华不会陷在成都和上海的夹缝之中而孑然一身?
这些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
但是有趣之处在于,女人们的讲述和男人们的讲述是完全不同的。
除开第一位受访者何老先生,陈建斌扮演的副厂长和作为主持人的赵刚显然都是成功人士,或许是我的误读,或许也是《渴望》以来的中国情节剧苦情戏的传统使然。
当然最精彩的段落是陈冲的20分钟——首先视觉上呈现为人物和人物旁边的镜像,而顾敏华和小花本身也是一组镜像,在加上陈冲这个集两个角色为一身的演员,实在是颇为精致的结构。
当然导演安排陈冲观看电视中《小花》的段落,于是这就呈现出一组“历史的镜像”,影片的结构意义从而也被揭示出来:那正是处在当下的人们对历史深处自己的回望,以及注目礼——是行礼,更是送别。
放在“第六代导演”的序列里,作为核心表征的“自视”依然在这部影片中占有重要位置。
不过《二十四城记》更像面对心理医生的一次访谈,结论,大概是最终的疗愈吧。
至于贾樟柯刻意不让身为易太太的陈冲打麻将,而让赵涛扮作王佳芝去香港跑单帮,只能看做是他的恶趣味……四、贾樟柯最后要说的则是有关“电影的事实”。
贾樟柯作为新科金狮导演和法国电影界的至爱,本片入围戛纳理所应当,但是获奖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评委大概完全不知道这部电影在说什么。
有趣的地方是本片在国内的某种程度上的悖反——评论以批居多,票房却是意外的好,上映三天过百万,虽不及某片和某片的一个零头,但终归是小贾老师的个人票房最佳了。
至于原因,我似乎可以抛出一个类似“后奥运时代电影格局”的概念。
这个过程大概要追溯到02年《英雄》开启的中国式大片时代,此后在《无极》形成怪诞的电影文化氛围,而电影观众回归理性之后,似乎有了“春季档”的概念——比如去年的《立春》和《左右》,甚至细微到“三八档”——比如《双食记》。
《二十四城记》号称也是三八档,当然这一切都与所谓“三代厂花”的剧情简介一样不靠谱。
而奥运会开幕式作为08年度第一大片,实实在在地展示了中国电影文化的深刻程度——有个冷笑话叫做中国是世界上最热爱电影的国家,因为中国连国歌都是电影插曲——而对奥运开幕式的评论,先批后赞,最后抓了央视当替罪羊,又成为终结华语大片时代的怪诞闹剧的标志。
我所谓“后奥运时代电影”大约伴随着院线的增加,公映影片的增加,影评作用的强化以及观众逐渐的理性观看。
02年到07年的狂欢客观上也培育了进一步市场和观众,而同时伴有的则是艺术片的逐渐浮出水面,随着电影文化的发展和资源的普及,看多了各国商业片和大众艺术片的观众也能够接受国产艺术电影了,这大概是本片小小票房奇迹的原因。
但是对本片批评的声音却很多。
看了一些评论,好像本片有不止一个版本——至少我今天在影院看的115分钟版本里没有华润的广告,没有赵涛哭着说我就想在24城给父母买栋房子这样的台词,我猜想大概是公映版本与宣传的免费版本的不同?
当然更核心的原因是,贾樟柯曾经作为一代文艺青年的必修课深入人心,而这些文艺青年未必接受这种影院的观看方式——贾樟柯的片子,应该是非主流的,被禁的,只能通过下载和盗版得到的,某种接头暗号式的存在,而如果他上了院线,就是堕落了——这大概是对一部分影评进行精神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可是不要忘了,贾樟柯根本就是一个看着港片长大的导演——而且电影说到底是要卖钱的。
现在回想起来,06年还上演过“《三峡好人》pk《黄金甲》”的喜剧,而所谓“观众”早已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但电影文化却实在短短几年间生根发芽,于是终于我们不再同一时间只有一部电影可看,于是“看什么”和“怎么看”也逐渐成了问题。
当然贾樟柯的形式主义仍然在考验观众——因为对这部影片,收回成本甚至赚钱都已经不再是问题,大约说到最后,觉得影片值不会票价的人也不在少数,是不是这也是批多于赞的一个原因?
然而我想说的是,在与宣传完全悖离的影片面前,似乎未经训练的观众难于找到一个立场,大概这又导向了“首周舆论决定论”。
五、二十四城记于是在只有4个人的小放映厅里,我看到了这么一部贾樟柯依然在关注流动和寻找的影片。
这部影片里充满着逝去的岁月的哀伤,它关于一个厂,一座城,一个国:这座厂可以是任何一个经历了和经历着中国当代史巨变的大型国企,里面有众多渺小的人,也有众多巨大的厂房和机器,有太多的悲喜日夜上演;这座城不是任何一座城,而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城市,它在这里降落,一如《孔雀》和《立春》里的鹤阳,而这座城市终于会消失,一如《三峡好人》里的奉节,在这里,这座城变成了资本洪流之中的一栋楼盘;而这个国家,是反反复复被讲述的中国,关于历史也关于未来,关于故事里的人和我们这些听故事的人。
你说历史是有意义的么?
你说是不是只有故事才是历史,还是历史本来就是需要被讲述为故事?
于是我们更愿意坐下来听一个故事,听那些远去的昔日荣光,听这个时代不断成长。
8 ) 贾樟柯的变动与哀愁
相比宁浩替第九城市旗下游戏所拍摄的短片《奇迹世界》,外界对贾樟柯与华润相结合、推出《二十四城记》似乎颇有微词。
原因在于宁浩被认定是名商业片导演,而他之前的小众作品无人知晓,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贾樟柯不同了,作为第六代的领军人物,他身上还扛着艺术电影的大旗不倒,现在大胆地向商业倾斜,总难免落人口实。
事实真是这样?
那如何去看待贾樟柯从地下时代到浮出水面的转变。
判断一部好电影,商业与艺术绝不是区分好坏的硬性标准,二者也不是势如水火,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更像无中生有。
在张艺谋时代,无论他怎么拍,没有手法上的批评也总要遭受道德上的质疑,那真是中国电影的两难局面。
如果宽容看待,无论《二十四城记》是命题作文还是长久构思,只要质量合格,主流满意,对于贾樟柯将来的身份多样和路线转变,影片的出现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变动《二十四城记》并非贾樟柯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它的两不像引发了激烈的观点冲突。
有人认为贾樟柯应该更加平实,用传统手法像《铁西区》那样去表现没落与变迁,拍出一部浩浩荡荡的纪录片。
这种指责拒绝了任何变动与突破的可能,而《二十四城记》恰恰是一部游走在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的电影,它用知名演员去扮演受访对象,讲述那些真假难辨的人生经历。
故事原型是真实感人的,但从演员嘴里说出来又带有不真实色彩。
整部影片就是如此奇异,给人嬉笑也带来感动。
《三峡好人》记录了三峡工程跟县城拆迁的互相影响,《二十四城记》也起到了相同的文化研究功能。
国有大厂420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终于支撑不住,接受了改变的命运。
表面上贾樟柯变得小心翼翼,用不同人的讲述碎片,尽可能地讨好所有人。
实际上他没有背离对于现代中国的关注,只是包裹的东西复杂了些,美学观念上受到了影响,比如演员的引入,令人联想到了房间内的假花。
假花能装点周围、美化一切,但是它的存在却破坏了整体的真实。
相比之前作品,《二十四城记》少去了常见的生活细节捕捉,一段段的口述史跟一篇篇的访谈录构成了它的主要内容。
诗句与演员互相配合,煽情手段也不再掩饰。
《二十四城记》比任何一部贾樟柯作品都要有感情,看银幕上不同的人儿泪水纵横,打出的诗句述说着一座工厂到一个城市的变动。
但在深挖掘与不修饰的层面上,在震撼观众的可能上,影片多少表现得有些力不从心,见好就收。
哀愁《二十四城记》用讲述人的年龄变化,带出了工厂命运和观念改变的必然。
这是一个独立的小集团,只因命运安排来到了成都;这是一个微缩的小社会,存活在中国的母体之内。
420厂和二十四城的背后都有一双大手,一双影响中国社会的手。
贾樟柯想用他的摄像机去充当眼睛,告诉观众,让他们看清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改变,就犹如把所有感情放在沉默的镜头中。
那时候的固定镜头长时间对准着420厂的工人,犹如给不同的人画肖像画一般,让观众有足够时间从正面去认清他们脸部的特征。
这种相对的静止起到了不断强调、强化印象的功能,放大了一个个人物所包含的细微魅力,与观众达成面对面的交流。
他们有的眼睛微微湿润,有的身体放松自然安详,有的还表现出不安与羞惭的神色。
人们对待420厂的情感,肯定不会变成二十四城崛起时的满心激动,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套房子去孝敬父母。
贾樟柯的哀愁也不仅于此,那样会变成廉薄的同情。
他的镜头景深里,依然有着数百成千的工人,统一身着蓝色制服,无论是进还是出,看上去都如此相似。
然后厂区里逐渐萧条,空无人烟。
门上大字被拆掉,更新换代。
老去的父辈跟消失的工厂,在淡淡的怀旧情绪和流行歌曲中,贾樟柯的哀愁油然而露。
这种哀愁放到结尾的俯瞰里,成都是如此迷人,但是它笼罩在一片薄雾里,身影迷朦。
迷朦里的命运,未来往哪里,这次的贾樟柯没有了超现实,但一样的是未来并不可知。
http://ent.sina.com.cn/r/m/2009-03-19/16052428366.shtml
9 ) 可怜贾樟柯,偷鸡不成蚀把米
观影前,我对《二十四城记》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除了那部装腔作势的《东》,贾樟柯算是一位从未引起我真正反感的中国导演。
我读了一点电影的宣传资料,知道是讲三线厂的兴衰。
这就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我就是一名三线厂的子弟,从小在东北人的群落里长大,对那种大厂的生活非常熟悉。
诗人翟永明参与剧本创作,吕丽萍、陈冲、赵涛,这样的组合也让我好奇不已。
我猜想,这可能是贾樟柯探讨女性命运的又一次尝试。
之前,他几次想进入女性的内心世界都铩羽而归,这次有了翟永明的加入,应该大有改观了。
结果……结果……看过电影的人都该知道,我所有的期待都落空了。
不是一般的失望,而是失望透顶。
贾樟柯拍的不是常规的剧情片,而是一部伪纪录片。
其实与电视台播放的那些纪录片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找几个人物做做访谈,闲聊一下往事和感悟。
剪辑的时候,主要是留下讲述者掉眼泪的镜头。
说的不好听,这种拍法非常媚俗,水平还在央视的《东方时空》之下。
唯一不同的就是,片子里有几个被访对象是由电影明星演的。
可能贾樟柯以为有明星助阵,这种平庸的纪录片也会有票房保证,但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应该知道,没有人会为了看明星坐在椅子上说话,就铤而走险买票进入电影院的。
何况,这些明星说的都是家常话,任何一名观众要想听,只要把自己平时说的话录下来就成了。
如果贾樟柯真的想保证票房,就应该想点靠谱的点子,例如让吕丽萍扮演同性恋,陈冲露出有纹身的乳房,陈建斌在澡堂搓澡不小心露出阴囊。
是呀,沉闷至死的艺术电影啊,除了色情镜头,我还能拿什么来拯救你?
实际上,贾樟柯自己也宣布了,他的下一部电影就是色情片。
唉,可怜的贾樟柯,你觉悟得还是太晚了!
这部戏已经把你主旋律的一面彻底暴露了出来,你想还有谁会相信你的电影会比《新闻联播》更意淫呢?
这是一部虚假的电影。
但并不是从电影明星介入才开始的,而是一开始就成了这样。
第一段是真实的纪录片,一位老工人不自觉地在镜头表演起来,倾诉自己对师傅的情感,然后接着两人相见,面对面老泪纵横,徒弟抚摸师傅的脸颊。
看上去很感人对吧?
这位徒弟已经很多很多年没见自己的师傅,如果他如此重情重义,为什么在摄影机出现之前这么多年都不看望自己的师傅呢?
这么简单的破绽,贾樟柯完全不理会,他要的就是落泪、感动。
接下来,吕丽萍讲自己死了儿子。
陈建斌讲自己失去了初恋情人。
一位下岗阿姨讲自己失去了工作。
然后陈冲出现了,讲自己失去了爱情和婚姻。
顺便插一句,陈冲的表演还真精彩,让我这个讨厌她的人也刮目相看,相形之下,吕丽萍和陈建斌那两段完全是垃圾时刻。
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陈冲的这一段,我会给这部电影打零分。
再之后,是一位成都的主持人讲自己的工厂经历,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还催人昏睡。
最后,贾导的红颜知己赵涛登台了,演出了整部电影里最糟糕的一段。
一位替阔太太购物的买手,讲述自己如何在某一时刻被感动,从而良心发现,懂得了体谅父母在厂子里消磨一辈子的辛苦。
总而言之,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勤劳善良,面对的都是不公的命运。
正如那位下岗阿姨所言,我们都没做错什么,为什么会遭此命运呢?
继《三峡好人》之后,贾导又成功推出了《成都好人》。
实际上,贾樟柯的电影总是这样的走向,好人被遗弃,都是命运总不济。
而罪魁祸首呢,贾导吞吞吐吐,说的含含混混:仿佛是现代化,仿佛是商业化,仿佛是全球化,仿佛是城市重建,又仿佛房地产热。
但不管是什么,还是那个祥林嫂的故事,掉着着苍白的眼泪,说着无力的言辞。
“我真傻,真的。
”“我已经捐过门槛了,真的。
”只不过,这样的祥林嫂故事被包装成了艺术电影,而且还是现实主义的。
想想真不容易,艺术导演好不容易在里面塞了那么多弱势群体的苦难,我们这些酒足饭饱之徒又怎么好意思说什么。
某种程度上,贾樟柯必须感谢国家电影审查制度,在一片可怕的荒芜之中,他坚持了这么多年的表面化、模式化的电影也成了“艺术良心”的一面旗帜。
然而,真的要仔细想想,从贾导的第一部电影,那些流行歌曲的符号就始终阴魂不散。
就是这么一点小玩意小伎俩,贾导乐此不疲,许多年过去了,如今除了勾起中年男女们的怀旧情绪,还能带来什么呢?
回想起来,我喜欢过贾樟柯的电影,但也怀疑过他的诚意。
真正的转折点就是看了他的那部纪录片《东》,那里面充斥着造假的痕迹。
我注意到他电影的特质,他顺从,喜欢动之以情,既没有意志抗争,也不是理性说服。
这一艺术上孱弱的表现令我觉得他远远不如《盲井》、《盲山》的李扬。
有时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高明的投机分子,一直利用文化符号表现“现实”,他其实并没有深入到“现实”中去。
不过,我一直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过于挑剔,以某种恶意在揣摩他人的内心。
但这部电影似乎肯定了那些长久压抑在我心头的负面评价,他是的,他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他假装思考,他也假装关切。
电影结尾意外地出现的是这么几行诗: “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当贾导让我们看到了那么多默默的失败,以及人们刻意掩饰自己失败的尴尬举动,难道他会觉得这是可以被另外一些人拿去“荣耀”的东西?
我们观看那些消逝的东西,卷走了别人的青春和梦想,这竟然会成为自己一生的荣耀?
这首诗是翟永明的朋友万夏写的,显然不是出于反讽,而是出于画龙点睛的需要。
其实依我看,这句话泄露的是贾导自己的心迹,他是被自己的平民情怀感动了,自我感动。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他又用电影抚摸了一把弱势群体,多荣耀啊,这是高雅的、艺术的荣耀。
10 ) 虽然我是工人的女儿
昨晚看了《二十四城记》。
如果说,“电影”是从“打算看电影”这个念头产生就开始的:《24城记》也开始得未免有点太早了。
中途又历经波折,好容易拿到票,坐在电影院里,去年看《三峡好人》那种无比激动的心情又再度回到我心中。
《二十四城记》如何?
诸位,我昨晚看完,直到现在才写这么点感想……这就是我的评语。
如今所有的导演都在进行伟大的尝试:就是试图打破“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的界限的尝试。
大部分导演采取的是这样一种策略:试图赋予剧情片以纪录片的质地,丰厚和真实。
《三峡好人》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二十四城记》试图进行的是反向尝试:在纪录片中安插剧情,故事就在讲述者的口中。
所有人都没有直接关系,他们的人物关系笼罩在巨大的命运下面:他们相互裹挟,相互观看,相互漠视,相互抚慰。
一点闪光的东西都没有吗?
当然有。
贾樟柯毕竟是贾樟柯呀!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小片段是两个人工人站在镜头前:其中一个年长的不断搔另外一个的脖子,直到对方笑出来。
那个笑容,那些面孔,实在是太生动了,让我感动不已。
但是,正因为是贾樟柯,那种“不够!
完全不够!
”的渴求,深植在我心中。
《三峡好人》开头那酣畅淋漓充满各种体液的长镜头呢?
举起一张十元人民币,放下时出现实景的天才想法呢?
更多的,那种气韵,气质,气息的东西呢?
并不是说我没有感动。
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工人的女儿,从小因为三线建设出生在四川。
可以说,电影里的点点滴滴我都太熟悉了:我爸妈的单位叫716,是搞潜水艇的,我们过去的番号是成字138部队,我们在四川的山沟沟里一住就是十七年,我们的单位有电影院,有子弟学校,有医院,还有豆浆厂!
我们也有保密费,我小时候经常能分到保密本儿。
我们也是走的奉节。
我妈妈,简直就是电影里那个沈阳妇女的影子:她老家是大连,十三岁随父母来到四川,再回东北,已经人过中年。
我感动了,我哭了,我看见那个下岗女工在公车上讲述她的艰辛,我看见赵涛讲那个在工厂里劳作的妈妈……泪流不止。
我的父母,是体力劳动者,当儿女目睹父母年事已高,还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那种心痛,也真的是像赵涛所说:是从内心里痛出来的。
但是这种感动太肤浅了。
我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寻求的绝不是这种“百姓人生”的感动。
我的感动被破坏了:我们祭典父母这一代人苦涩青春的方式,难道只是买一套“24城”的房子?
这是贾樟柯第一次在电影里使用职业演员,他采取了一个小心翼翼的方式:正如很多导演在电影里掺杂了非职业演员在职业演员中,他恰好相反:他将职业演员掺杂在非职业演员中。
陈冲,吕丽萍,陈建斌,扮演了三个老厂的职工。
有时,贾樟柯的电影里会出现少许“有些过”的东西,比如《三峡好人》里的小马哥,是有些造作的。
但是在《三峡好人》这种湍急如大江大河的电影里,少许的败笔一闪而过,但是在《二十四城记》这种静止的电影里,那些瑕疵,不,我不认为是仅仅是瑕疵,而是缺陷的东西,却被放大了。
陈冲扮演了一个叫做“小花”的厂花,她说自己因为长得像陈冲得了这么一个外号,真名反而不被人所知。
镜头外的人(是贾樟柯自己吗?
)问:“那你真名叫什么?
”我们的陈冲笑着说:“我叫顾敏华。
”全场大笑。
是为了这种幽默感吗?
不,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幽默感。
观众们大笑的时刻,是察觉这是“扮演”的时刻,也是梦醒的时刻。
也许这正是贾樟柯所要的:他要一种间离的效果,要这种浅薄的幽默,要观众明白,不要那么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即便是你愿意相信。
但是,我只是感觉到,我被嘲弄了。
陈冲演得不错,就像吕丽萍和陈建斌,他们已经演到了一个职业演员所能演出的最好。
但他们不是“大丽”,也不是“顾敏华”,那么,我们如何面对真正的,被隐藏在电影后的,也许真的存在的“大丽”,“顾敏华”呢?
我深爱贾樟柯。
这是我苛责的原因,也是我失望的原因。
我开始审视和逼问他拍摄《二十四城记》的动机,而他的电影动机,在之前,我从未怀疑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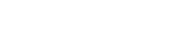
尝试模糊记录与剧情片界限,真实采访的情绪感染力与职业演员演绎的“间离效果”互动。对历史和记忆的探究,对后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被遗弃和遗忘悲剧历史的关注,以有素朴质感的电影语言和固定机位长镜头表达。
成都 成都
你大爷的,就他妈电影版冷暖人生。甲鱼,你去死吧。你丫要煽情,就到电视台干编导,没必要这荼毒中国电影。
“越老的工人越在维护这个体制,绝不是他对这个体制没有反省,没有批判,而是他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
一帮假模特。
镜头感差,形式缺陷导致诉求点无法突出
精准有余,卖弄过度
不要再说“几粒职业演员坏了一锅汤”,你看他们多么卖力地不让你看出来他们是在演呀
陈冲的段子最有喜感……
想到了《心如折纸》 纪实又电影,结合得很好。更本不是为了票房而拍的电影,真的很棒!
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看得我要困了
精致点和缩水版的《铁西区》陈冲其它客串实在是勉强
想起了我的爷爷
还是吕丽萍演的最好
到底算伪纪录片还算伪电影,奇奇怪怪的做作
拍的跟CCTV的纪录片似的
纪录片请换掉专业演员,太别扭了他们。
还不错,赵涛最差,吕丽萍其次,陈建斌跟陈冲抖不错
好吧 我承认那几个演员的确十分别扭